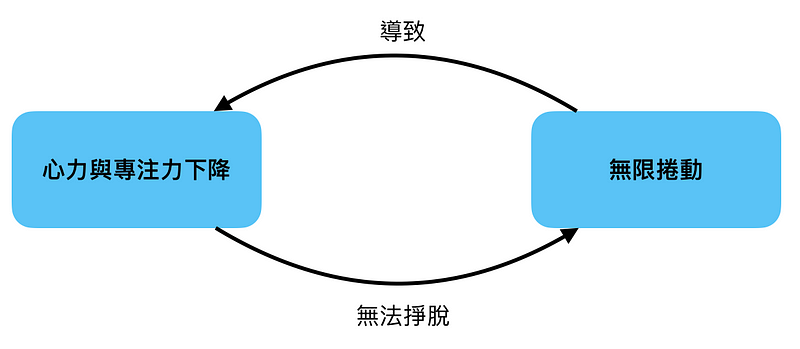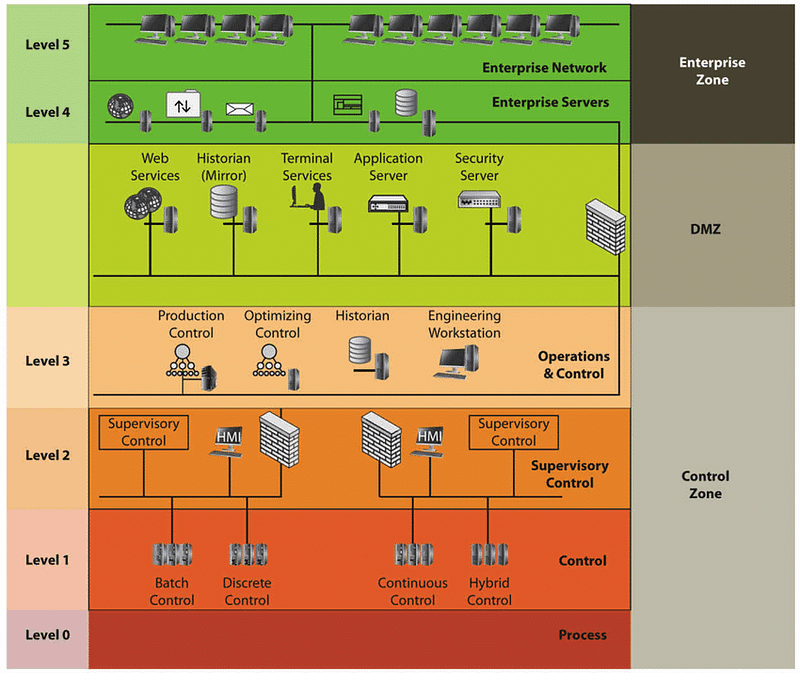今天聽什麼:家庭裡的議題倡議與討論

今天在聽不好意思請問一下的我們來處理一些南京沒有處理完的問題。
會知道不好意思請問一下這個節目,是因為主持人致昕同時也是報導者的記者,聆聽報導者的 podcast 時有時會聽到他好聽的聲音。因為自己聽 podcast 十分注重說話聲,因此對他溫柔舒服的聲音與說話方式特別有印象。近期得知台南的午營咖啡在疫情期間收起來,轉型成 podcast 時,才意外知道致昕是午營咖啡的創辦人之一,以及他有在經營自己的 podcast 頻道。高中時曾去過一次午營,很惋惜它收起來了,但也很開心它能在線上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分享議題,以及聽到致昕的聲音。
話說回來,這集 podcast 是我聽的第二集,第一集是不是沒有用的年輕人。這兩集的內容都是訪問青民協(臺灣青年民主協會 TYAD)的育萌。高中的我可能也算得上是某種程度的憤青,在學校裡搞學權,二二八當天午休借會議室播〈傷痕二二八〉,沒有任何學生來,被我人情勒索的朋友坐在台下睡覺,只有快結束時一個老師站在門外,握著我的手告訴我我在做的事情很重要。在校外交朋友、搞串聯,辦跨校模擬公投,放學開完票,再揪團去喝酒,或是更久以後半夜哭著在電話中說沒關係,隔天披著彩虹一起上街遊行。這些經歷讓我選擇了先點開關於青民協與育萌的這兩集。
Podcast 裡,育萌提到他如何與家人談論公投議題,讓我想起自己嘗試在家中與父母討論社會議題的經驗。我家是那種表面開明治理,但其實父母與子女的上下關係又如傳統家庭那般明確的類型。對生活意見的反駁或討論都很難在餐桌上說出口,自然更不用說社會議題和選舉投票了。
家庭內的倡議,比起對外倡議困難許多。對外倡議時,不用在乎與他人互動的方式(只需要遵守基本禮儀),也不用承擔關係緊張甚至破裂的成本。每個倡議的對象都與倡議者關係甚淺,絕大多數根本互不相識,因此不論他要聽、不聽,或是吵到面紅耳赤,一天過去,心情平復就沒事了。但在家裡,子女與家長的互動模式早已在長期的相處中根深蒂固,如果互動模式裡沒有建立起彼此溝通的方式,如何溝通便成了討論或倡議前需要先克服的難題,這個難題可能比討論與倡議本身更難。
我最初與家人討論的嘗試,是與我媽討論同性議題,並試圖說服他去投公投。放學開車回家的路上,坐在副駕駛座的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才開口問我媽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也許是我太緊張,或者單純不夠成熟、缺乏經驗,當我媽說他不同意,要求我嘗試說服他的時候,我就慌了。每天都在關注網路上最新的論戰,與朋友一同檢視誰的論點合理、誰在胡扯,公投內容的來龍去脈、主流討論的脈絡我都記的一清二楚,但我還是徹底地慌了。因為我找不到一種對話形式來訴說我的觀點。「我應該要嘗試講道理嗎?」但我的互動模式裡不存在向爸媽說理這種事,因為說理就是頂撞、就是吵架,小孩只要負責聽就好了。「我應該要嘗試分享身邊朋友的故事嗎?」但我不認為他會把我說的遙不可及的案例當作真的,儘管那是真的。我缺乏他會相信我的信任。我也不認為我能說好一個故事,好到足夠讓不同意變成同意。「那我應該怎麼辦?」最後我以自己為例,說了一個「如果我是同性戀呢?」的例子。後續討論不了了之,很快就結束在一片靜默裡。但現在回想起來,在我舉出這個例子的時候,討論的模式就從不曾存在的「討論」,回到了「要求」甚至是「哀求」的狀態。我用一種小孩要糖的方式(那時我已經高中了),要求我媽接受我的觀點,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和我媽「討論」。除此之外,當時的經驗也體現了這個議題在我家庭裡的缺乏,我完全不知道我媽在這方面曾有的相關經歷與想法,便很難從他也許能夠接受的角度切入。但我還是很感謝我媽在表達不同意後,沒有直接切斷討論,而是願意給我說服他的機會。
昨天下午在客廳看電視時,新聞報導賴清德提出補助私校二萬五學費的政見,我媽碎念「私校都招不到學生,要退場了」之後,轉過頭來問我有什麼看法。這次我平靜地與他分析退場機制與學費補助之間的差別,以及資源反向重分配的問題,好好地把我的觀點講清楚了。我和我媽之間出現了討論的模式,而他的碎念讓我得以理解他的觀點和想法,並以此回應、說明我的觀點。
為什麼我們之間突然就能夠討論了?我還沒想清楚。也許我即將大學畢業,年紀夠大了,我媽終於把我當作能夠討論事情的「大人」。或者其實沒什麼理由,只是一次意外,剛好就這麼對上線了。又或者他主動有意詢問我的意見,因此釋出某種願意聆聽的氣息,使得我下意識地得以說出口。我不知道,但我還是很感謝他願意與我討論這些事情。
(這些只是我個人對於自己家庭的觀察,我媽和其他家人一定會有不一樣的觀點和想法。)
後記
不小心說了一個開頭很慘、結果很美好的故事,莫名有點反感。
直接寫名字(致昕、育萌)有種奇怪的親密感,我並不認識他們,他們肯定也不認識我。但又覺得這樣的親切感很好,而且 podcast 裡也都這樣稱呼,所以就決定是這樣了。
雖然上一篇說了一堆要練習寫技術文章的原因,但真的靜下心開始寫字的時候,冒出來的卻都是各種與技術無關的生活心得或想法,不過這樣也很好。
依然會在公開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想法時感到心虛、害怕,特別是多了從自己的角度、單方面揭露家庭裡的事件。在想這是不是在為其他家人代言,使他們相對於我缺乏聲音,沒有辦法被公平、公正的認識。前陣子讀〈老派約會之必要〉體悟到,壞與惡本身也源自於缺乏他們的視角與聲音。但暫且先這樣吧,反正這裡也沒人看,有機會想清楚了再來思考怎麼調整。